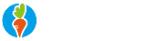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一块圣地,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在挂掉之前要去的地方,要做的事情。这个地方是宏伟壮丽的大峡谷、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汹涌咆哮的印第安纳波利斯500英里赛车场,是庄严肃穆的紫禁城,是巍峨壮阔的万里长城。

1
爸爸的梦想从我是孩童时期就没有变过,他说出来都是斩钉截铁,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
我要带我的三个孩子去打圆石滩。
这句话他说了一遍又一遍,他对我和两个哥哥说过,夏天夜里在外面乘凉的时候他对邻居说过,每周四他们球队活动的时候,他对球友们说过,甚至在酒吧里和坐在旁边醉醺醺的陌生人,他也说过。
每次爸爸说的时候,我们都点头称是,我们要站在18洞的发球台上,看着左边的太平洋热烈拥抱圆石滩的海岸线,苏格兰诗人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称赞:这是陆地和海洋最美丽的相遇。
我们还不止一次设想:站在7号洞发球台,俯瞰被太平洋波浪簇拥的狭小果岭,那个世界上最美丽的短三杆洞,会不会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样美。
我们预定了一次还是两次,甚至可能是三次圆石滩行程,最后都无疾而终,计划总赶不上变化。
我要带我的三个孩子们去打圆石滩。
生命中很多这样的事情,等待太久,当时的冲动已经消退,最后只剩下终生遗憾。多少人,多少事,还有多少地方让我们想起就会微笑,会大笑,会哭泣,对我来讲,所有的一切就是圆石滩。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本文原发于2019年父亲节),父亲节,我来到圆石滩,来到美国公开赛,百感交集。那个骄傲、倔强又有很多缺点的男人,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他在七年前去世了,在他说了下面这句话两年之后:
我带着我的三个孩子们打了圆石滩。
2
我最早喜欢运动是因为爸爸。爸爸热爱运动,并且把这个基因送给了我们兄弟三人,我们又传给了他的孙辈们,成年之后,这个大家庭从来不缺少体育活动。
夏天,爸爸和他的朋友们每周四会打夜间的高尔夫联赛,这些人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里面有我们的亲戚,我打的小联盟的教练,还有几个爸爸一生的好朋友。爸爸个子矮小,圆墩墩的,所以他的挥杆很紧凑,爸爸的上杆十分缓慢,慢到你都可以趁机给你的汽车换机油。
我的两个哥哥都打高尔夫,爸爸从小就把这个热情种在了我们心底,我们喜欢和爸爸一起打比赛。
我喜欢棒球和篮球,每周五晚上看橄榄球比赛。但是在秋天和冬天的周末下午,就是高尔夫。
我清楚地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痴迷高尔夫,就是30年多前的美国公开赛。1988年在Scranton郊外的一个小镇上,一个11岁的男孩坐在家里的地下室,和爸爸一起看电视直播。那是柯蒂斯-斯特兰奇第一次在美国公开赛夺冠,转播结束的那一刻,我拿上爸爸给我改造的5号铁,开始在院子里模仿柯蒂斯的挥杆。有几个球打得和柯蒂斯一样直,但是也有几个直接飞到了街上,我听到了外面汽车的急刹车声音,他们不知道那些球是塑料空心的。
1988年美国公开赛就是我高尔夫的觉醒,从那天起我没日没夜地在院子里打塑料球,不断地听到外面的急刹车,从5号铁到挖起杆,到木杆,最后是一个1号木。我在院子里设计了我的18洞球场,包括最后一个决定胜负的五杆洞——开球的时候需要越过我家房顶。
爸爸有时候会坐在院子旁边的木凳子上看我打球,看着那些掀起的草皮,不知道他作何感想。
我在爸爸的悼词中写道:看我们打球是爸爸最开心的时候,他喜欢去看棒球比赛、篮球比赛、田径运动会和汽车拉力赛。在我高中篮球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身体的某一部分已经崩溃了,我是球队年龄最小的队员。当终场哨响起的时候,爸爸意识到看自己孩子打比赛的时光已经结束了,爸爸没有活更久,看他的孙辈们在各项体育活动中生龙活虎。所以一有机会,他就会看我在院子里打球,可能会有一些时候,他会想到那些被球砸到的木头椅子和千疮百孔的草皮。他会嘟囔两句:看看你把草坪弄得乱七八糟。
但也就这样,他只会走到阳台里面,把那个木头椅子拖过去一些坐进去。他的心不够硬,不能说出让我停止打球的话。我会在打球间隙告诉他,老爸,等我工作挣钱后,给你买一块新草坪。
不过我从来没有兑现这句承诺。
只有两次真的把他惹恼了,第一次我忘记把草丛里的球捡起来(有时候我会用一些真球练习大角度挖起杆),老爸剪草的时候剪草机碰到了这些真球,当剪草机的刀片碰到了这些老化的橡胶和塑料,那种声音你一辈子都不想再听到,这时候他对着房间里骂了一些不文明的话。
还有一次我在18洞果岭上错失推杆,我觉得那是杆的问题,我翻出来他的钥匙,在爸爸的皮卡车上找到了跟随他很久的那支推杆,用完之后忘记放回去了。周四晚上当他去打夜间巡回赛的时候,在第一洞果岭就发现自己的推杆不翼而飞,我只能说他当时并没有特别愤怒。
3
在我准备向我的妻子求婚六天前,爸爸去世了。他去世后很长时间,我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给他打电话的习惯和冲动,我想告诉他我对喜欢的姑娘求婚了,然后她同意了。想告诉他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想告诉他我想去哪里,我想做什么……这种情况持续了差不多一年,尤其是当我去一些著名高尔夫经典赛事,当我去那些著名的高尔夫球场,那些鬼斧神工的设计和大自然完美融合的球场的时候,我总是伸出手就想给他打电话。
爸爸喜欢我的职业给我带来的故事,每次他都会把我的故事和旅行告诉他的伙伴,我去了哪些地方,见到了什么样的人。我回家的时候,还没有开口讲一句话,家乡的人们已经知道我所有的故事。他们还知道我的哥哥们,知道他们读了什么学位,做了什么工作,他们的家庭什么样子。
爸爸一直为他的三个儿子骄傲,他讲我们的故事,穿我们给他带回来的衣服。他向他的朋友们吹牛,他的衣服上有很多很多标志,有二哥阿兰送给他黑黄相间的VCU(弗吉尼亚联邦大学)衬衣,二哥穿着横贯北美追随他的公羊队比赛;他在镇子里穿着LSU(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颜色的衣服,戴斯泰森(Steson)牛仔帽,那是我们大哥克里斯给他的,克里斯是上面两个学校的法学教授和系主任。当然最多的就是带有ESPN标志的衬衣、汗衫和挡风头套。爸爸穿着这些衣服到处游逛,无论是吃早点,出门喝一杯还是去上班。我们送什么他就穿什么。只有一次我和他发生了争执,我告诉爸爸,你不能穿着VCU的高尔夫球衫在平安夜去教堂,得稍微注意一下。
过去的一年,我有太多的事情想告诉爸爸,想告诉他,我站在奥古斯塔12洞的发球台上,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铺满了整个球道的样子,想告诉他在辛耐科克的美国公开赛上,USGA有一个星期忘记了开喷灌头,以至于果岭像玻璃一样滑不溜手,很难停住球,想告诉他在苏格兰的球场,顺风的时候,4号铁就可以打出260码,但是逆风的时候,1号开球木却只能打出190码;甚至想告诉他周五在莱德杯(2018年)比赛开始前45分钟,观众已经迫不及待地高喊Allez!!Allez!!(法语“加油”)
运动是爸爸送给我的礼物,同事他还给我对高尔夫的热爱。只有一件事我不会向他提及,只有一件事他不会希望借助我的双眼来实现,我从来不告诉他圆石滩是什么样子,因为:
我带着我的三个儿子打了圆石滩。
4
当你走过高速检查站,沿着17英里大道行进的时候,你的心跳开始加速,你的肾上腺激素开始分泌。如果说圆石滩风光秀丽,就和说巨石阵很古老、帝国大厦很高一样词不达意。在这里人行道上迈出的每一步,走过每一个突然的转角,都会重新定义人间的完美。
沿着曲折起伏的海岸线,海浪轻轻地触摸沙滩,道路两边的树木巍峨高耸,温暖咸湿的海风在你耳边轻轻拂过。我们开着车子,两边的豪宅古堡、奇松怪石不断闪过,心里暗暗发誓,一旦中了彩票,下一分钟就要来这里买一套。那一棵棵柏树大概都有250岁了,和周边美丽的风景融为一体,神秘,让人不忍亵渎,时间在这一刻好像都静止了。
终于我们来到了这里,把车停进了停车场,我们走向前台。哥哥报了我们的姓名,我们的家族姓氏(Pietruszkiewicz)每一次都会有些小麻烦,基本上都会要求我们重新说一遍,用字母拼出来。然后大家都会好奇地问:你们祖籍哪里?你们花了多长时间来学习拼写自己的姓氏。哥哥也和往常一样开我们姓氏的玩笑,这个15个字母的姓氏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话题。这时候我往右边一瞥,看到了阳光下的第18洞,我走了过去,下来了台阶,推开门,站在阳台上往外面眺望。
这就是圆石滩,我们梦寐以求的圆石滩,她的美丽和我们想象的一样,我一见钟情。
我们来了,所有的期待,所有的憧憬这一刻美梦成真,我们定好了房间,订好了航班,租好了车子,确认了开球时间。
我们来到了我们的酒店,登记入住,分配好房间,订好了几点吃晚饭。
突然,我们发现爸爸不见了。
我哥哥在房间后面的一个小露台发现了爸爸,露台不大,只能放几把椅子,看不到任何球场的风景,也看不到辽阔的太平洋。这不是圆石滩宣传册上面那种海景露台。但是这个小露台同样让人感到很特别,就是那种一旦去过,你就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哥哥发现爸爸的时候,这个老头子在哭泣。但是看到我们,他就偷偷抹去了泪水,不承认他刚才哭了。我是一个比较爱哭的人,小时候我的好朋友去家里接我,告诉我爸爸他今天要在球场削我。爸爸总是说,对我儿子好一点儿,他有些多愁善感,他很爱哭。
爸爸好像从来不会哭。
但是圆石滩让他老泪纵横。
5
蒙特利半岛上的天气变幻莫测,有时候大雾弥漫,有时候海风呼啸,让你有扔掉手中的高尔夫球杆去放飞风筝的冲动,还有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飘来的大雨倾盆。
我们第二天醒来,圆石滩的上空碧蓝如洗,万里无云。太阳照着蔚蓝的太平洋上,波光粼粼。
我们在酒店的餐厅俯瞰一号洞发球台,一组一组的球员从那里出发,我们知道,再过一会儿,就该轮到我们了,这么多年的等待,这么多年的憧憬,我们终于来了。
两个哥哥开始去练习场热身,那个时候我对练习场有一种执拗的避讳,我不在下场前练球。我如果在练习场打了几颗臭球,就会在脑海里种下魔鬼。所以我和爸爸就在练习场后面等他们,爸爸坐在推杆果岭旁边的凳子上,我在果岭上推了几下,问爸爸他要不要来推一推。
“我不需要练习,我知道怎么推杆。”爸爸这句话已经说了不知道多少遍,炉火纯青。
我继续我的推杆练习,体会延迟释放和4英尺推杆。这时候我看了一眼,凳子上已经空了,老爸不知道去哪里了,过了几分钟,还是没有见到他。大概十分钟之后,我再次望向板凳,这时候爸爸回来了。
他嘴里吃着巧克力棒,头上戴着一顶崭新的帽子,一看就是刚从专卖店里买来的——一点儿也不合适、甚至可以说有些丑陋的一顶圆石滩logo帽子。
爸爸耸耸肩,笑着说,根本管不住我自己,就买了这顶帽子。
接下来的5个小时,我们徜徉在圆石滩球场,我们不停地照相,我们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今天,这个高尔夫的圣地属于我们。我们的球童不断地提醒我们,喂喂,大哥,该你打球了。我们一路左顾右盼,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完全忘记了我们是来这里打高尔夫的。
我们来到圆石滩之前打其他球场,老爸总会跳过一洞不打。他才60岁,从来没有认真照顾过自己,他的身体很早就不在鼎盛状态了。在我们这次高尔夫朝圣之旅的前几站,在半月湾(Half Moon Bay)和远眺山(Spyglass Hill),他都会休息,坐在球车上或者站在果岭边看他的孩子们打球,心满意足。
我永远忘记不了他脸上那种志得意满的表情,他一手把这些孩子拉扯大,把他们带进高尔夫的大门,现在一家子四个男子汉整整齐齐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真的很满足。
在圆石滩,他也放弃了一洞不打。他在15号洞离开果岭50码的地方,一杆切进,抓下小鸟,所以他奖励自己休息一洞。球进洞的那一刻,老爸扔掉球杆,振臂高呼,我们也跟着一起沸腾起来,他的圆石滩梦之旅不但终于成行,还有小鸟在歌唱。
直到他去世前,他还和我开玩笑:那天,他比单差点的小儿子抓到的小鸟还要多。
我保留着那颗球,就在爸爸的办公桌最底下那个抽屉的角落里,这是我们家里的办公室,我基本上每天都在桌子前面坐着。有时候我会打开抽屉,拿出那颗球,我会靠在椅背上,一手拿着球,然后看着墙上面的照片,上面就是17英里大道上面的一棵柏树,这条大道的尽头,就是圆石滩。
6
我不是在精心修剪的球道上长大,也很少去造访设施完备的练习场。爸爸经常会为此而感到愧疚,他有时候会平静地说,对不起,儿子,爸爸要是哪个球场的会员就好了。我有一阵儿球打得特别好,幻想着能去大学里打高尔夫联赛,进一步降低自己的差点。爸爸经常会懊悔,如果我们是乡村俱乐部的会员,你的球肯定可以打得更好。
他不知道,其实并没有那么差。从我在家里院子的球场到后面的山上有一条羊肠小道,那就是我2871码长的球场,攻果岭的时候不要尝试温波利山(Wemberly Hill),球停不住。在夏天的时候也尽量不要往果岭上打球,进去了就找不到。我的这个球场感觉就像USGA在美国公开赛上的设置,球道艰难、果岭飘忽,很难打。
爸爸还教会了我如何找球。我们经常去的球场第一洞左边是一排排的树林,高尔夫的一个通病就是一号洞综合症,看看老虎第一洞的开球乱飞能占多少比例你就知道了。在这里,如果你的上杆快一点,下杆时前面的肩膀转得快一点,再偷偷看一下球的起飞路线,这些基本上可以保证你打一个鸭脖子一样的大左曲。刚开始我在这里打飞的球爸爸总能找到,后来别人打飞的,我能找到。每周四爸爸开球前的一两个小时,他就会钻进这片树林,花上半个小时,有时候能找到十几颗球,当然有时候只有两颗,出来笑着说,应该可以找更多的,但是我只挑了好球。
刚开始我没有球的时候,会去爸爸的球包里翻出几颗。后来,我接管了家族的生意,接替爸爸钻进树林里去找球,把那些大左曲的产物纳入囊中。
球场上的人我都认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里面有T骨、扎扎、乔伊和爱德华叔叔、波先生……我在那里学会了打球,我会和哥哥们一起打球,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和爸爸以及他的朋友们。和爸爸他们在周四晚上同组打球是我至今为止最清晰的记忆,打完九洞之后,爸爸会坐在2号洞果岭后面的露台上,看我们打1号和2号洞的加洞赛,会有一两个美元的彩头,我们会一直打到天黑看不见为止。
周四晚上6:30之后,所有的高尔夫礼仪都不再适用。保持安静?你可算了吧,球场上人声鼎沸。最多四人一组?谁想加入就可以在发球台上架Tee直接开球,只要能在11人组的球道上找到你的球就好了。
2号洞果岭就在那个露台的下面,每当十几个人把球攻上果岭,准备拼抢这几张一美元钞票和今后几天吹牛资本的时候,爸爸从来不放弃任何说风凉话的机会,但是当我推杆的时候,不管他还是下面十几个人是不是刚刚说过俏皮话,我都能感觉到爸爸很安静,他太想自己的儿子取胜了,无论是我在高中,大学,还是参加工作以后,他都是这样全力支持自己的孩子们。
爸爸自己的打球就不会这么认真,他的上杆像蜗牛一样慢,打出的右曲球让人怀疑人生,想着这位先生是不是要打一个掉头球。但是爸爸从来都不会慌张,慌张是我的特点。
但是我见到他慌张过一次,是在举世闻名的斯鲁普公开赛(Throop Open),被人们视作第五大满贯。这是我们镇子上一个延续四周的赛事,是一个有差点的比赛,我那个时候读八年级。之前九洞比赛我从来没有打进过40杆,但是那次比赛的前三周我打出了连续三轮39杆,对于我这种长年在联盟中被虐的球员实在是让人扬眉吐气,我在领先组昂首进入最后一周决赛。
最后一天,困扰所有高尔夫球员几个世纪的问题在我身上同样发生了,我开始胡思乱想。那九个洞我打得很挣扎,我记得爸爸非常平静,即使是我在第8洞眼看着就要上演让-范德维尔德1999英国公开赛大崩盘的时候,爸爸还是很平静。我那个洞果岭边的切杆切得太大了,但是果岭上飞奔的球却被洞口挡了一下,救帕成功,我长舒一口气。走向第九洞开球台的时候,不经意间瞥到了爸爸,他开着球车跟着我,我看到他对着空气说了一声OK。他不会对我说,不会对任何人说,但是他的心里十分渴望我取胜,他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希望他的三个孩子是最好的。
7
那一天电话响的时候,我没有接。妻子和我那天突发奇想,我们驱车90英里去芬威公园看红袜队的比赛,在球场外我们简单吃了点儿东西,就一头扎进了嘈杂的球场。我们找到座位刚坐下的时候,口袋里的电话响了。是爸爸的电话,我决定先不接。我们的电话经常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会问我新车开的怎么样,会跟我抱怨菲利斯总也跑不完全垒,或者在电话里暗示我该回家看看了。大部分时间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后面总是有很大声音的体育比赛背景音,有时候这些声音甚至会盖住他的讲话。
当时我想在看完比赛回家的路上给他回电话,30分钟后,电话又响了。我接了电话,这次里面不是爸爸,是我们的邻居。他告诉我,爸爸现在医院。从上一次生病以来,爸爸一直在服用血液稀释剂。那天早上爸爸倒车的时候追尾,脑袋撞了一下。几个小时以后,他就不行了,邻居把他送到了医院。
邻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只是断断续续听到了几个单词,脑出血,马上手术,但是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些。
邻居说爸爸想要和我讲电话,接着听筒里就传出了爸爸的声音,他说得有点慢,但还是他的声音。爸爸告诉我不要担心,说他头痛。我告诉爸爸我和妻子现在已经上车,现在就去宾夕法尼亚。爸爸说不要,他很好。我说我们马上就到,他说他很好。这时候我听到爸爸身后嘈杂的脚步声和说话声,知道他马上就要进手术室了。我告诉爸爸我爱他,我很肯定我说了。后面连续好长时间我都不断地问妻子,挂电话前我说了我爱他,我说了,对吗?
这是我和爸爸最后一次讲话。
爸爸进行了脑部手术,接着又做了一次。尽管有那么多有才华有爱心的医生和护士,爸爸还是再也没有醒过来。两天后,他去世了,享年69岁。
邻居说在准备手术的时候,爸爸只有一个要求,他要和他的儿子们打电话,一个一个地打电话。邻居帮着他一个一个地找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电话里说了我爱你,爸爸。
葬礼上,我们的亲戚、爸爸的朋友、同事还有那么多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一个个地向我们致意,在哭泣声中和一句句节哀顺变之间,两件事情被反复提及。
你们兄弟三人是你爸爸的骄傲。
他一直在给我们讲你们圆石滩的故事。
8
我们没有意识到爸爸的圆石滩之旅采购了那么多纪念品。在葬礼上以及后面的两个星期,我们遇到几十个人告诉我们,爸爸从圆石滩给他们带了礼物,带有圆石滩标志的球标。这时候我们三个面面相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行的购物活动。
他希望给每一个人讲述他和三个儿子圆石滩的故事,所以他给他们带了带有圆石滩标志的小礼物。他知道,他给别人球标的时候,别人自然而然地就会问起这次圆石滩之旅。
这时候他就可以开始讲述自己和三个儿子的圆石滩故事,他会讲在17英里大道的早上,凛冽的寒风要冻掉我们的鼻子;他会讲我们在外面10℃的时候我们开着敞篷车出去兜风;他会讲我们打完球晚餐的时候,我们会喝掉多少半瓶红酒,他讲这些的时候一定会哈哈大笑,因为我们从来不会点一整瓶红酒,我们就是半瓶半瓶地点,润杯,再点;他会讲我们晚餐的地方,望出去就是辽阔的太平洋;当然他不会忘记吹嘘自己那个神奇的小鸟,让强大的圆石滩拜倒在他的脚下。
最后他会告诉人们,在18洞果岭上结束之后,我们互相拥抱,他对他的孩子们说的一句话:
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
葬礼上,亲友们排着队和爸爸告别。最后到我的时候,我拍着爸爸的肩膀,告诉他我会想念他,告诉他我爱他。
我在他的棺材里放了两样东西:一张他和三个孩子们的照片,还有他在圆石滩买的那顶帽子。
(文、图/Nick Pietruszkiewicz 翻译/Bigmouthe)
译者后记:
写过很多文章,翻译过很多高尔夫文章,有很多特别感人的故事。没有一篇像这一篇一样,让你笑,让你流泪,让你想到自己的父亲,让你想到自己的儿子。这里面是不是高尔夫,是不是圆石滩,一点儿都不重要。是一个平凡的爸爸,和他一样平凡的三个儿子们,一起去完成一个梦想。甚至是否完成这个梦想,也不那么重要。有了这个梦想,人生就有了希望,就有了我们激情燃烧的日子,就有了我们平凡的感动,就有了我们一生的回忆。有时间就多给爸爸打个电话吧。献给所有的爸爸和儿子们。
标签:
版权声明:本文由用户上传,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