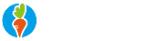对于澳大利亚的学校领导来说,远程学习只会给本已复杂的工作增加一层复杂性,这些工作的职责包括注意义务、合规、财务和人员管理、风险缓解等。

事实上,很少有工作像校长这样复杂和苛刻,在封锁期间,有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对教育专业的尊重和信任有所增加。
然而,澳大利亚教育的问责制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顽固的单向流动,教育官僚分析、评估和批评学校校长,而那些高层则不受这种审查。
根据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ACU)教育领导力高级讲师Paul Kidson博士的说法,如果口号“我们都在一起”有任何意义,情况肯定不应该如此。
在过去的 20 年里,澳大利亚的公共教育官僚主义显着增加,公共教育倡导组织“拯救我们的学校”(SOS) 在 2020 年的一篇研究论文中透露,系统和学校层面行政人员的增加远远大于教师和学生的增加。
除了担任校长12年之外,Kidson还是教师和校长工作量的研究人员,包括参与澳大利亚校长职业健康,安全和福祉调查 - 这些调查一直记录了全国过度劳累的学校领导的高度压力和焦虑。
Kidson博士说,他想知道,如果澳大利亚各地的教育部门要求教师和校长完成一项关于澳大利亚教育系统表现的调查,他们将如何了解自己的表现。
“该系统向分析、评估和批评开放的一个令人信服的原因是,它对其主要利益相关者(如教师和校长)这样做。因此,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肯定会有一个公平的问题,“Kidson博士告诉教育家。
“如果我们真正致力于将此作为国家的共同利益,那么对鹅有益的东西肯定对鹅有益。
基德森博士说,即使是“婴儿步骤”也会大大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有一些令人鼓舞的发展正在进行中,但仅限于中层领导层面,”他说。
“目前,教育领域的重大决策是由没有或非常有限的直接学校教育经验的高级领导层做出的,但他们在没有咨询领导者的情况下制定政策。
基德森博士说,通过媒体发布而不是事先听取部长们的简报来了解政策,只会侵蚀教师职业和官僚机构之间的信任。
“需要有一个持续的说法,即教师受到重视。你不能继续把更多的压力从系统降到学校,“他说。
“我们需要优先考虑教育的人文和社会因素。
Kidson博士说,ATAR和NAPLAN已经证明自己在大流行期间不那么重要,该系统应该询问如何减少对学校施加的一些压力。
“技术只会加剧这个问题。没有重大证据表明远程学习期间技术的爆炸使教师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他说。
报告显示,除了给年轻人带来健康和行为问题外,大流行期间过度使用屏幕还导致许多教师和领导者的数字疲惫。
叙事必须聚焦“国民教育”
Kidson博士是澳大利亚独立学校校长协会(AHISA)的长期成员,他说,整个澳大利亚的教育仍然“深深植根于狭隘的问题”——如果我们要看到任何有意义的变化,另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例如,没有一致的入学年龄,不同部门在各自看待教育的方式上相当细分。最后,人们的勇气说教育是一场值得战斗的战斗,“他说。
“然而,我们看到教育的竞争激烈。这是错误的游戏。真正的游戏是关于社区中的人性,关于同情,希望和勇气。
基德森博士说,围绕“国民教育”的新叙述可能是一条可行的前进道路。
标签:
版权声明:本文由用户上传,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